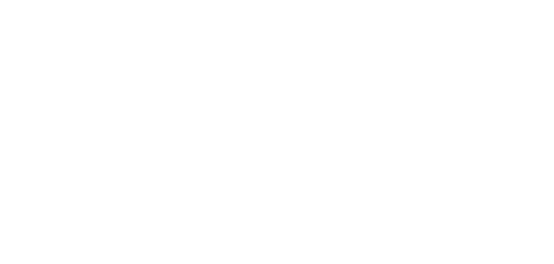报恩寺那口古钟
汤养宗
没有一种存在不是悬而未决。在报恩寺
我判断的这口古钟,是拮取众声喧哗的鸟鸣
铸造而成。春风为传送它
忘记了天下还有其他铜。天下没有
更合理的声音,可以这样
让白云有了具体的地址。树桩孤独,却又在
带领整座森林飞行。这就是
大师傅的心,而我的诗歌过于拘泥左右。
永不要问,这千年古钟是以什么
力学原理挂上去的。这领导着空气的铜。
潘维:
我个人认为,国内有几位诗人,他们以非主流的独特性树立了自己的风格,比如汤养宗,比如余怒。他们处理题材,几乎都避开诗歌正面、整体的角度,他们走的是“旁门左道”,而恰恰是这种非俗套,让他们脱颖而出。汤养宗的这首《报恩寺那口古钟》,第一句就显示了作者的视觉思想:“没有一种存在不是悬而未决”,不解释,直接抵达,这就是诗的方式。整首诗,诗人的认知围绕着主题穿行、伸展:微妙的触及、点到为止、自恋情结,这是一首充满了中国古典神韵的现代诗。
当金色黄昏升起
韩文戈
每个人都注定被另外的人所谈论,回忆的片段
那是我们的熟人,或曾经的熟人
就像晴天有人说起阳光,而另一些人会谈论雨
众口不一:他们分别在不同时刻
走进我们自以为漫长的生命
当我们像过冬的岩石坐在大陆腹地,经受风吹
大海一刻也未曾停息,花朵继续包围着我们
而那些关于我们的话语会在尘土里静下来
我们的熟人已开始谢世,他们带走了时间的絮叨
新的一代有如长大的树木排列在地平线上
被我们看到,也被我们听到
属于他们的话题:日月照临新世界
这正是我们要么好好活着,如同濒危的植物
要么带着一生的爱恋
赶在天黑前离家出走的理由,当金色黄昏升起
刘波:
这是一首与相对性有关的诗。现世和历史、动与静、新与旧,包括代际之间的更替,每个人都是在二元世界里寻找安慰,寻求平衡。而人生经历与体验如何转化为自我对世界的认知,的确是既生动又复杂,韩文戈理解了生活给他带来的改变,这种改变看似针对独特的个体,其实也覆盖了所有被生活追问过的人。诗人在中年困境和内在冲突的交织中写下了他的感悟,并将此纳入到自然界的循环体系,而这种妥协式认同里又潜藏着隐秘的抗争之意。
当我们在谈论别人的时候,自己也可能在被另外的人所谈论,主体与客体的置换让这种体验迅速变成了一道哲学命题。人生开始陷入回忆,各种片断纷至沓来,熟人或曾经的熟人,都像经常谈论的天气一样,注定要如过客般介入我们的生命历程。我们静下来领受自然的馈赠时,自然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,我们唯一能感受到的,就是当下瞬间成为了历史,它们以永恒的方式定格,并构成新的话语“在尘土里静下来”。置身于中年反思的现场,熟人已开始谢世,他们“带走时间的絮叨”意味着什么?无法再重新来过的人生,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了“殇之痛”,但“新的一代”如同树木开始在地平线上成长。代际更替的残酷与感伤,在诗人笔下被表述为必须的选择:在“日月照临新世界”时,要么好好活着,甘愿承认变老的处境,要么“带着一生的爱恋/赶在天黑前离家出走”,这似乎是浪漫主义的抵抗,既对接于现实,也存在于想象之中,此时,当金色黄昏升起,人也必定会面对自然的淘汰。韩文戈以个体的感知代很多人道出了难言之隐,而陌生化的诗意在绵密的修辞里戏剧性地生成,如同自然本身成为他审视自我和世界的参照,所有的观念、情感和意图都可能是他完成这一人生使命的动力与中介。
另一个肖氏
小 海
肖斯塔科维奇
左脑边缘
有个像子弹片的
金属碎片
虽然很痛苦
可他极力反对取出
因为这个碎片
肖斯塔科维奇
头每次歪向左侧
脑海里会跳出新旋律
他马上记录下来
就这么诞生了
许多曲子
其实,碎片
也可能阻断了什么
可医生说
脑子的碎片跟着头动
位于大脑颞叶部分的音乐区域
就会受到压迫而响应
如果取出碎片痊愈
健康正常的
肖斯塔科维奇
民族乐器有哪些?